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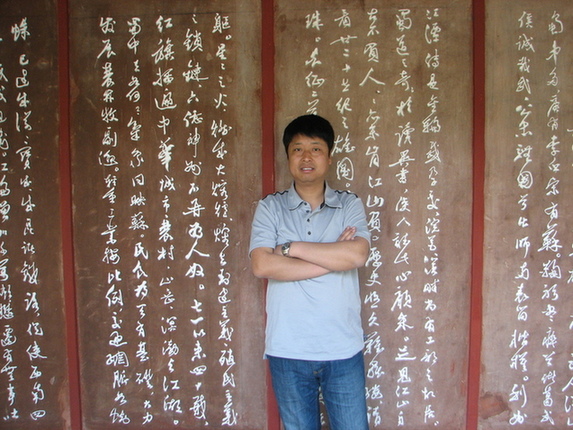
好友晓军的生活,令人十分羡慕。当我们天天陷于社会情状而昏头昏脑时,他却忽而神出鬼没,徜徉于山水之间;忽而意态萧闲,共行于名流之旁;忽而兴致勃勃,荐书于友朋之中……当我们整日忙于人事纠纷而牢骚满腹时, 他却几十年如一日,对案自揽,操笔弄墨,平心静气,也不见抱怨。
晓军常说:艺术就是一种趣味么。他性好游,闻佳山水辄神往。爱怀古,常羡古人风骨。比如他引嵇康句说: “游山泽,观鱼鸟,心甚乐之。 ”这大约可以理解为在人迹不到、水草清茂之处徜徉容与,是人世间最为赏心悦目的事。但他又引元代大画家黄子久之言: “终日只在荒山乱石,丛木深筱中坐,意态忽忽,人不测其为何。又每往泖中通海处看急流轰浪,风雨骤至,水怪悲诧而不顾。”这便让人觉得不是赏景,而实有庄子化蝶的意味,人要化于景中了。
和晓军同游久了,觉得山水对人也亲切和善起来。但晓军除了享受美景外,却在寻找一种作画的素材,一种精神上的感悟。我们看一座山,看完后便抛之脑后。晓军却在寻找捕捉知觉与反应中间那刹那的停顿,贮于脑海笔尖,并有所选择的创造出一个影像,以满足自己作画的需要。我们亲近一条小溪,在那溪中嬉戏完了,那条溪就在我们的脑子里隐去了。晓军却在感受那其中的生命精神。他说:山能解语,鸟亦知情,泉有情调。这让我们感知,自然中也有生命,有精神,有情绪感觉意志,和我们的心理一样。我们知道,艺术家要模仿自然,并不是真去刻画那自然的表面形式,乃是直接去体会自然的精神,感觉那自然凭借物质以表现万相的过程,然后以自己的精神、理想情绪、感觉意志,贯注到物质里面,使物质而精神化。晓军的画里,通过笔墨勾发出藏在心中的情态来,其背后有动人的生命情怀:山峦秀美博大,树姿楚楚可爱,屋舍积沉岁月,岸石饱刻沧桑,使一般的山川草木体现出一种生命气息,使我们的生命由狭窄的现实扩大到自然的生命情怀。我想这是晓军对待自己的创作所要求的基本的美学诉求。
晓军说,他也常常地感觉,这个年头儿是不是可以画着这样的画?可见他有迷惘的阶段。有人曾说,美术是民族的集团的而非个人的艺术,所寻求表示的也是传统的而非独创的美。集团的美术之根据最初在于民族性的嗜好,随后变为师门的传授,遂由硬化而生停滞,其价值几乎只存在技术一点上了。在今天看来,绘画已脱离集团(虽然它生于集团)而个人化了。但晓军也深知,个人是个人化了,但并不等于完全可以脱离传统,买椟还珠。这个人化的艺术,在晓军看来,正是要反映这个时代的特点。宋元明清,佳作如云,但那属于古人和那个时代,而不属于21世纪的我们。检讨这个时代,或许就是在当下之中反抗当下,在人生之中反思人生,在自然的破坏之中重新追求自然。毋庸讳言,中国思想传统中之所谓 “万物一体” 与“天人合一 ”在工业化信息化的时代已与我们渐行渐远,但我们又不得不厮混在这个时代,我们当下的社会、人生、艺术如何与被破坏的自然重新融凝合一,如何使自然回归自然和精神回归平静,正是要被提出、表现、倡导的。这是晓军的山水作品首先给出我们的意见和倾向。但同时,在时代的同步中,他的山水作品又表达出个人的美学诉求和主张,这种诉求和主张又暗合普罗大众的精神理想。东晋郭璞注《山海经》时所说的: “物不自异,待我而后异,异果在我,非物异也。 ”但物又为什么会因我而异?恐怕是因为“我”的精神追求。这个异,便是晓军个人化的精神表达。 我们经常从晓军的作品中可以考见他的性情嗜好。这个性情,就是对山川田园的向往;这个嗜好,就是对精神平静的渴求。然而这种精神表达,又何尝不是今天生活在城市的人群的集体诉求?有时我们看一幅画,而不能神游其中,如历其境,则不能了解这幅画的美。 晋人向外发现了自然,向内发现了自己的深情。观晓军的画,常有这种感觉。 有的画家的画是超人性的,它没有人的气息,晓军与之相反。他现时的作品,常见有三种,一是纯自然的表达,一是田园牧歌式的描绘,一是小品式的率性。纯自然的表达,画中可见泉石之美秀,峰岭之俊拔,云树之缥缈,鱼鸟之飞跃,斧劈石数叠,清泉绕其下,清溪巉岩相与激荡,浑然而成一自然世界。田园牧歌式的描绘,在水边林下发见藩篱村落,屋舍帆樯,莫不历历在目,而恍若身游其中,使人又去画中小住的冲动。他的小品,缥缈润泽,气韵流动,藉此一口生气,灌溉其中,自致清虚,崇尚空灵。然而他所崇尚的空灵,并非 “率意顽空者”,而是必须 “以坚实为空灵”的基础,意随景到,笔借目传,如闲中花鸟,意外烟云,真有一种人不及知,而己独知之意味。但寻其笔墨,又似一无所有 。
方士庶在《天慵庵随笔》里说:“山川草木,造化自然,此实境也。因心造境,以手运心,此虚境也。虚而为实,是在笔墨有无间。” 晓军的笔墨,不事铺张,不事雕绘。他的山水风格,不故为艰涩以托于古奥,不摭拾浮艳以破坏法度,不刻意规模以失其本真。他用色极少,用笔极简,用墨极淡,不以规模尺寸争短长,只以含情笔墨现心声。其一山一石之姿态,一草一木之细微,皆有所感发于心,情著乎笔端,或意含于画外,使观者觉一草一石间风回水萦,自有佳致。他营造的山水田园,可游可卧,自然可亲,经得起我们慢慢地抚摩赏玩。
我经常嬉笑道:晓军心里恐怕住着个隐士吧。 他居在市中而自隐,身在俗间而自雅。他广涉书话典章、诗词艺文、民情风俗以至奇闻趣事,我们又彼此熟稔,只消片言只语,便能相互会意。有时相坐对谈,酒浓耳酣,他渐入开悟的境界,漫说自己的闻见,时有通透旷达之语。他不为喜怒所羁绊,也不为外物所烦扰,正如他的画,随着学识增长,简练与淡远并在一处,敦厚与宁静映出纸外。宋画家米友仁说:“画之老境,于世海中一毛发事泊然无着染。每静室僧趺,忘怀万虑,与碧虚寥廓同其流。”晓军的创作状态,现时正走进与碧虚寥廓同其流的化境。他告诉我:生命中最美的东西,常常是跟自己对话的,不是表演的。我也知道,他的美学修养的状态,其实最大的一部分是个人内在孤独的时刻,因为只有在独自面对自己的时刻,才是那个审美的我、真正的我。
《梵网经》有云:“如狮子身中虫自食狮子肉,非馀外虫,如是,佛子自破佛法,非外道天魔能破坏。”今天的书画市场,那种炫耀技法、恶好猎奇、自以为是、肤浅虚空的“自破佛法”之流的所谓作品,我们见得太多。晓军现时厕身于名手之间,不急不慌,泰然处之,不拘泥于陈法,也不任意妄为。我知道他内心坚定而自信,淡泊而坚守,他心中有自己的佛,他已做好与佛对话的准备。我愿用陶公的一句诗赠他:“衣沾不足惜,但使愿无违”。(叶峰)